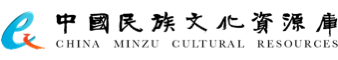

2017年11月,第14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上,达斡尔族传统服饰绽放于呼和浩特的舞台上。 资料图片
上世纪80年代之前,人们认为传承达斡尔族文化是政府和专家学者的事情;21世纪前10年,人们认为传承达斡尔族文化,各地达斡尔学会是新生力量;如今,各类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,文化微信群层出不穷,所有热爱民族文化的人都可以通过键盘或拍照的形式,记录下传统文化的变迁。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书写“民族志”的新时代。
新吉玛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
今年7月,笔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新吉玛的文章——《达斡尔民族手工艺文化的挖掘、研究与传承》,文中介绍了她为传承达斡尔族刺绣文化所作的努力:一是她向母亲学习绣荷包,间接学习外祖母的刺绣技能;二是她向周围手艺人吴英花、斯布乐玛学习并与之合作;三是她培训学员,这种传承方式已超越家庭传承,以一种广阔的胸怀去发展达斡尔族刺绣文化。
新吉玛的达斡尔族服饰设计,难得的是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。她研究老年人的绣法,探究外祖母遗留下来的鞋面,成功地绣出几乎一样的作品;她还原书上记载的女性“满式达斡尔头饰”,制作男性元宝帽;她研究传统刺绣方法,记录了绣法的达斡尔语称呼,如伊乐嘎提萨比(平绣)、得日斯乐吉袄衣贝(缬绣)、述日库贝(盘绣)、好么撇么乐伊乐嘎(折叠绣),还有锁绣、堆绣等技法名称。
达斡尔族文化丰富多彩,但达斡尔人记录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并不长,流传下来的文化史料不够丰富。据了解,达斡尔人撰写的第一本史书是花灵阿的《达斡尔索伦源流考》,距今仅有170多年。
对于达斡尔族来说,对本民族文化的全面体认,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、达斡尔被确立为单一民族以后的事情,距今不到70年时间。近70年来,达斡尔族的文化水平与时俱进。尽管随着全球化、信息化的到来,民族文化受到了冲击,但达斡尔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中来。
达斡尔族文化仅靠口耳相传,曾有过断裂的现象。不过,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流动中发展的,我们既不能盲目地崇古,也不能忽略传统,而应该尽可能把祖辈们留下的东西记录好,如能传承且创新则更好。
新吉玛等人就是抢救、保护与传承达斡尔族文化的重要参与者,她在探索一条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。过去,我们对民族文化重视不足,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。如今,新吉玛等人通过各种方式传承达斡尔族优秀文化,这种努力值得尊重。
《莫日根姐姐》与民族文化传承
去年,微信“达斡尔族文化艺术群”展开了关于歌曲《莫日根姐姐》的讨论。这是达斡尔族妇女跳“哈肯麦”时唱的歌曲,广泛流传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。对于这首歌,到底是“莫日根额克”,还是“莫日根姐姐”,大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。
“莫日根”是英雄、猎手之意,“额克”是姐姐之意,“莫日根额克”就是猎人的姐姐。用达斡尔语“莫日根”与汉语“姐姐”组合而成“莫日根姐姐”,这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是否妥当?
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景区工作人员乌嫩库齐介绍,老艺人都唱“莫日根额克”,个别年轻人唱“莫日根姐姐”,并且现在有一种趋势,以前唱“莫日根姐姐”的人正在改唱成“莫日根额克”。达斡尔族民歌类书籍都把这首《莫日根姐姐》命名为《杭给》或《莫日根姐姐》。
但讨论还没有结束。有人认为,“莫日根额克”中的“额克”是“哲哲”的音变而来,原型是“莫日根哲哲”,是模仿猎人驱放猎鹰时发出的呐喊声。答案到底是什么?这需要达斡尔族民歌方面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。事实上,达斡尔族文化艺术在传承过程中,有一些内容已很难弄清它的真面目。比如,达斡尔族萨满祭词中的一些含义,已很难解释清楚了。
不久前,笔者参加了一次纳西族东巴文化讲座,在讨论中大家提到,东巴经有很多内容是不可翻译的,彝族毕摩经书里也有不可翻译的情况。也就是说,有些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有一定的神秘性,或者说保密性,需要留白,不作解释。如果这种认知具有普遍性,那么达斡尔族萨满祭词存在很难翻译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。同样,达斡尔族民歌中一些很难解释的词句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。
这样讲并非强调民族文化的神秘性,我们应该对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保持敬畏之心,因为对于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,先人们积累文化十分不易。
我们希望能继承祖先所有的文化遗产,但必须清醒地看到,有些文化与我们渐行渐远,有些文化可以继承,有些文化也可以改造、创新。
《伊如木罕》与民族志写作
前段时间,笔者读到苏雅的文章《伊如木罕》,颇有感触。这篇文章文风质朴,叙述风格淡定,情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这无疑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《伊如木罕》主要讲述了作者的姥爷和奶奶面临人生归途时的态度。面对生死之事,达斡尔族人的心态与普天下人的心态是一样的,而其中的不同,也许就是在准备归途的过程中,他们所体现的对天地鬼神的认知。
“伊如木罕”是达斡尔语,汉语译为“阎王”或“地狱”“阴间”。在《伊如木罕》中,苏雅对奶奶准备“归途”的过程描述得十分细致:奶奶50多岁就开始细心准备这些物品,从7件套殓衣布料到用小布袋装好入殓时的各种物品……作者无意于创作一篇民俗文章,而是要通过姥爷、奶奶的生死观来表达自己对生死的态度,这在文章末尾说得很清楚:“我这种从容面对死亡的心态应该是姥爷、奶奶熏陶出来的吧……死亡是任何人躲不了的结局,与其谈虎色变,不如坦然去面对。”
这样的讲述,已经具有了民俗学价值。达斡尔族葬礼民俗,以往我们都是从民间故事、百科词典、调研资料中获取,这样的具体讲述很少。尤其令人惊异的是,文章提到了“大酱块”。据了解,“大酱块”出现在民间传说《尼山萨满》中。《尼山萨满》是在东北达斡尔、满、鄂温克、鄂伦春、赫哲、锡伯等民族中广泛流传的故事,在达斡尔族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基础。
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意义在哪里?当一个作家拿起笔来时,应该站在一个客观角度进行书写,他要记住自己作家的身份及其使命。这种身份是广义的作家而非狭义的民族作家,至于他笔下写什么,是否写了他的民族,那只是一个客体对象。换句话说,不能因为某个民族没有出现大作家,就说这个民族的文学土壤不够丰富。无论哪个民族,哪怕是人口较少民族,同样会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。达斡尔族作家李陀、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已经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还具有民族志意义。一个民族的文化选择应交给这个民族的百姓来定夺。老百姓有文化选择权,他们作出的种种文化选择,本身也属于文化发展。对于爱好写作的人来说,拿起笔记录时代的变迁,就是他们的使命。当一些民风即将消失时,人们记录下曾经的生活画面,就是对历史、对祖先的尊重。
当今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,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幸运的是,很多人已经加入到传承民族文化的行列中来。达斡尔族民间文化活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此起彼伏、绵延不断,这是社会的进步。人们关注自己的群体,关注身边的文化,寻找作为主人的主体存在感,这是民族文化的觉醒。我们欣喜地看到,达斡尔族文化在觉醒,更应该积极地对其鼓励、引导,让更多的达斡尔族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)
来源:中国民族报